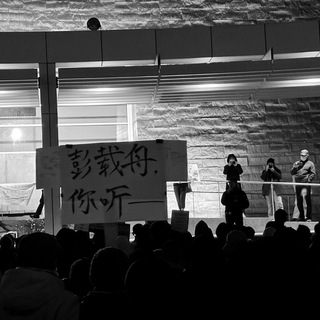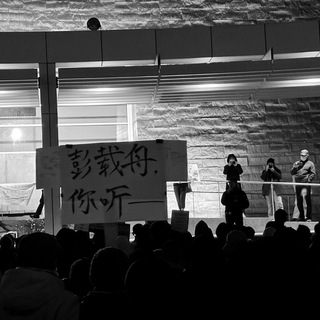2022-04-22 01:32:54
俄国内外的社会科学学者.对于运用“极权”一词形容后苏联俄国都嗤之以鼻。就连“威权”都有争议。镇压开始后不久,“混合政体”(hybrid regime)一词逐渐流行起来。最初的用语是“非自由民主”(iliberal democracy),由记者法里德.札卡利亚 (Fareed Zakaria)在一九九七年的一篇文章里提出。札卡利亚强调民主做为一种透过自由及公开选举选择政府的方式,与自由主义这项保卫个人自由的政治计划之间,有所区别;两者并不必然携手并进。政治学理论长久以来都承认自由专制政体(liberal autocracy)存在,例如奥匈帝国。如今则该承认其结果也必然存在。札卡利亚引用了白俄罗斯、吉尔吉斯和秘鲁,以及其他国家的例子,这些国家的民选领袖不断侵犯宪法为保障个人自由而设定的权力限制。他也提到俄罗斯正面临这样的风险:1993年,鲍里斯.叶尔钦出名地(而且名副其实地) 攻击俄国国会,攻击行动是由国会自身的违宪举动所引发。接着他停止宪法法院运作,拆解地方政府体制,开除数名省长。从车臣战争到经济方桉,叶尔钦习惯性地表现出对宪法程序及限制的漠不关心。叶尔钦很有可能本质上仍是个自由民主派,但他的行动创造了俄罗斯的超级总统制。我们只能盼望他的继任者不会滥用它。
“非自由民主”观念有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一旦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开始限制自由,就不太可能继续拥有真正自由开放的选举——即使事实上,选举仍定期举行。毕竟,就连苏联都有选举,根据苏联宪法第九十九条规定,此为不记名投票的直接选举:“禁止对选民的意志表达进行监督。”然而在鄂兰的命题中,就提到了极权政体如何剥夺臣民的意志,而再没有比选举制度更实在的呈现了——在苏联参与投票的每个候选人,全都能够顺利当选。
在普丁统治的俄国,多数选举都被完全消灭了。州长和参议员如今都是官派,下议院则由政党按选票比例组成,泰半消除了个人投票的意志。自2000年以来,每次选举的总统低选人,实际上也遇不到反对。尽管如此,还是有旗帜、看板、音乐会,以及其他选战所需的配备,也有投票。虽然看上去更像是西方民主政体了,但实际上却更像苏联。过了一段时日,“混合政体”一词取代了 “非自由民主”。
在俄国,“混合政体”一词是由青年政治学家叶卡捷琳娜.舒尔曼 (Ekaterina Shulnan) 普及起来的。她写道:
混合政体是在新历史时刻里的威权政体。我们知道威权政体与极权政体的差异:前者奖励被动,后者则奖励动员。极权政体要求参与,要是你不参加游行,不跟着唱歌,你就不是忠诚的公民。反之,威权政体则试图说服臣民待在家裡,任何太热衷游行、太大声唱歌的人都是可疑的,不论歌曲思想内容或游行方向为何。
舒尔曼重申了胡安.林兹的定义,针对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做出差异,但省略了他对极权主义“完全政治化”与威权主义“非政治化”本质的区别。舒尔曼写道,混合政体是冒牌货,但西方观察家们往往只聚焦于假冒的其中一个面向:假冒民主。“很容易就能留意到,民主的门面是纸煳的,”她写道:“但更难理解的是史达林的肌肉粘贴在上面。”她论证,普丁政权所动用的武力总量,按照二十世纪的标准其实微不足道。十几个政治犯之于极权主义恐怖,意义正如普丁每四年当选一次之于民主政体运行。她主张,混合政体借由策略性地以不同程度同时模仿民主与极权,来延续其生命。
其他用以描述普丁政权的词语,还包括盗贼统治(kleptocracv) 和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纳瓦尼“骗子小偷党”主题的变体。一位名叫巴林特.马札尔(Balint Magvar) 的匈牙利社会学家,拒绝接受这此用语.因为他强调“盗贼统治”和“裙带资本主义”两者部必然包含某种自愿结盟,个人仿佛能够参与裙带系统或选择不参与,然后还能自主地——即使获利较少——做自己的生意似的。但霍多尔科夫斯基和流亡国外的寡头们,乃至不知几千几万入狱或破产的企业家月,其命运都表明了这种想法纯属谬论。
马札尔出生于一九五二年,在匈牙利这个压迫相对较少的东欧集团国家长大。这使他得以接受良好教育,成为一名社会学家。但马札尔在1970年代晚期开始积极参与地下反对政治,因此遭受惩罚:他被禁止在大学任教、禁止前往西方国家。1980年代晚期,马札尔身为自由民主联盟匈牙利自由党的创始人之一,成了国家民主转型过程的一部分。到了2000年代,自由党逐渐失去政治地位,最终不复存在,马札尔重回社会学研究。而在维克多/ 奥班 (viktor Orban)的新政权下,他再次被大学院校列为不受欢迎人物,于是也再次专注于研究东欧各国社会。
他强烈厌恶“非自由”之类的用语,因为这些用语聚焦于那种政权所不具备的特征——像是自由媒体或公平选举。他认为这种用语宛如借由“大象不会飞”或“大象不能游泳”之类的说法来描述大象,这完全没提到大象真正的模样。他也不喜欢“混合政体”一词,这在他看来仿佛是模仿出来的定义,因为它根本无法定义这个政权表面上混合了些什么。
马札尔开展出目己的概念:“后共产黑手党国家(post-communist mafa state)”。这个名称的前后两半都很重要,“后共产”因为“民主大霹雳(democratic bild bang)之前的状态,对于体制形成有着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它从共产独裁的基础上产生,是共产独裁衰败后所剩的机骸组建而成。”后共产国家的统治菁英最常出身于旧体制职官权贵,无论是党内还是秘勤部门。但在马札尔看来,这还不是这些国家最重要的共同特征。最要紧的是,一些旧势力集团演变成以单一个人为中心,由该人带领整个集团掌握权力。巩固权力与资源相对容易,因为这些国家直到不久前仍由一党垄断权力、由国家垄断财产。由此产生了独特的情境:
在其他专制体系的例子里,或者….私有财产被转换成近似于国有财产,或者财产的正式分配多公未被触动.……但在历史上找不到这样的先例:国有财产根据可疑的规范而全被转换——至少在这些规范的社会接受度这方面是可疑的。当意图是创造出一层私人持有者,那就仿佛是意图从鱼汤里养出鱼来。
这些集团夺取的财产与权力,并没有其他显而易见的合法持有者,这使得他们的工作出奇简单。
按照马札尔的定义,黑手党国家不同于其他由一人统治、一小撮菁英圛绕于领䄂身旁的国家。在黑手党国家里,达个小小的权力集团结构就像个大家族。家族的中心是家父长,他并不统治:“他处置——地位、财富、身分、个人。”整套体系的运作宛如共产时代分配经济的讽刺画。家父长及其家族只有两个目标:积累财富、集中权力。家族般的结构严分阶序,家族成员身分只能经由出生或收养取得。在普丁的例子里,他最内圈的亲信由从小在列宁格勒街头和柔道馆一起长大的人们组成,第二圈包含他在国安会/联邦安全局的同事,更外圈则是他在圣彼得堡市政府的同事。他在极罕见的情况下会“收养”某人进入家族,像是原先默默无闻的装配车间领班霍曼斯基,一举被提升到某种第三代堂表兄弟的身分。一个人不可能自愿离开家族:他只能被驱逐、被断绝关系和被剥夺继承权。极权主义国家的两大支柱——暴力与意识形态,成了黑手党国家手上区区一个工具而已。
355 viewsedited 2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