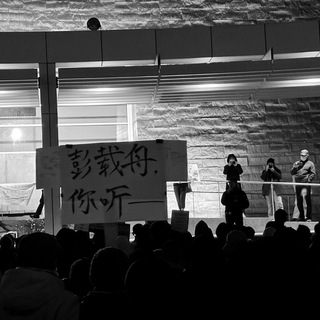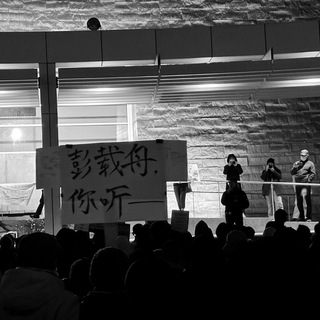2022-07-09 12:39:38
任谁的人生被不了解人生的人去评判解构,都是件可悲可笑事。
至今许多人为张爱玲叫不平,好心疼,叹她不如自己心明眼亮。萧红也受如此待遇。今时余秀华也受——条分缕析,凿凿言之,惋惜关切,高傲至极。
可是命运有分工,有人极需人生浓烈,认为所谓平顺是乏味浪费、不值一过的——人却视勇士为弱者,施以怜悯,教诲谆谆,全不觉自己可笑,真是奇观。
再至于小说,被不懂什么是小说的人读,也不是任何一方的幸事。
雪莉杰克逊《有花生的寻常一天》,不光小说好,钱佳楠的译后记都好,范式传统,情感现代,并讲明了杰克逊小说的命运——从未停止收到读者的愤怒、质疑和指责。
所以原来也不只是现在,也不只是我们,在将小说当成许多种其它物件,偏偏不是小说。
许多人读小说,总怀着与自己相关的期待,当小说是贴心侍者,或父母亲,或占星师,街头艺人,魔术师——美丽的杂耍,悉心安慰,明亮预言——小说应当只为取悦他的已知,肯定他的观念。
如果你感到小说冒犯了你,它冒犯的并不是你(这个人),而是未经思考的生存、伪善的美丽面孔、懦弱的谎言共谋和狭隘可怖的秩序。但......假如这些东西就是你,那它冒犯的就是你。
奋不顾身者的人生也在冒犯着鄙夷舍身、求生求全之人,于是后者要作解释:他们是昏头了,他们缺乏我所拥有的人生经验。
这些热心人,从不愿想到那最为可能的一种真相:他并不想过与你同样的人生。
那些饱受冒犯的读者,也不愿明白甚至哪怕闪过一秒钟的猜测:这小说并不是为了愉悦我而作。source
67 views09:39